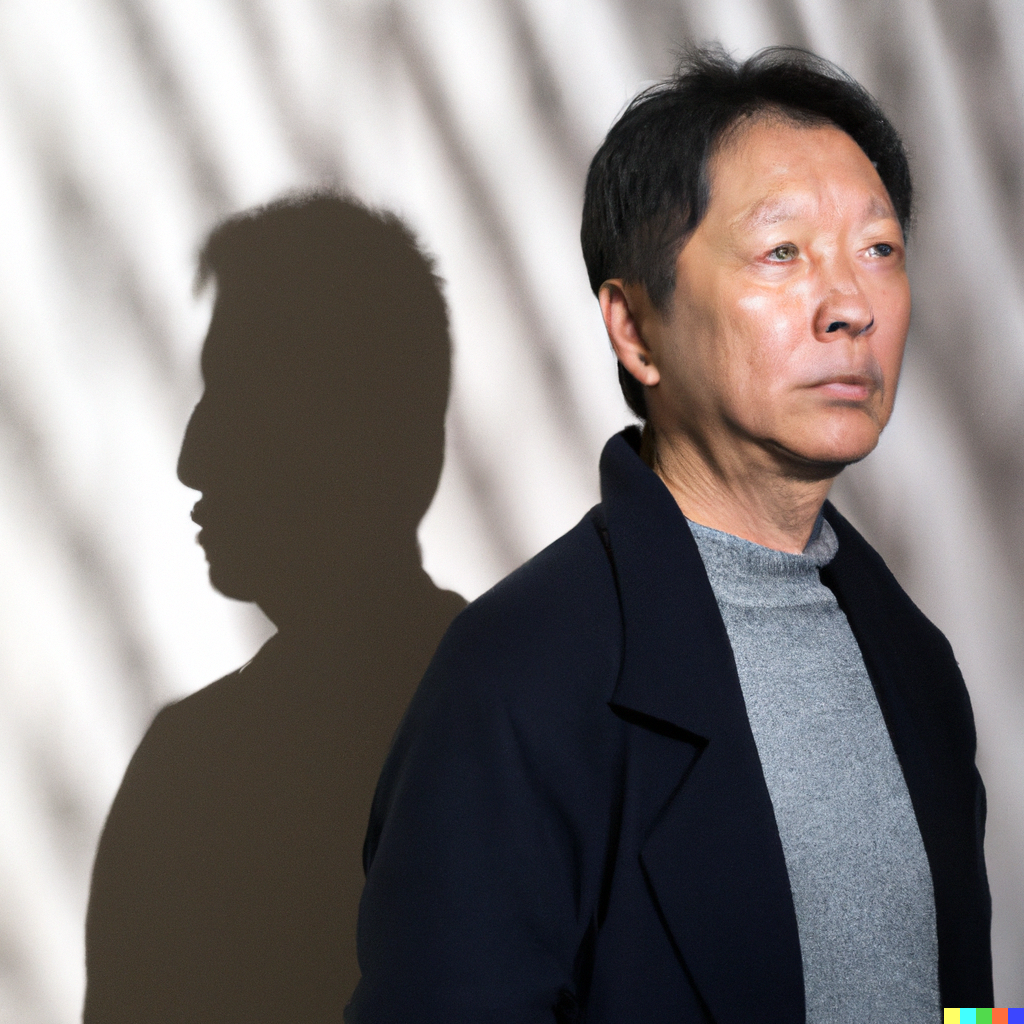詮釋(interpreting)不該被生下來的人:想開啟人生新篇章時孤獨被冒犯後 (四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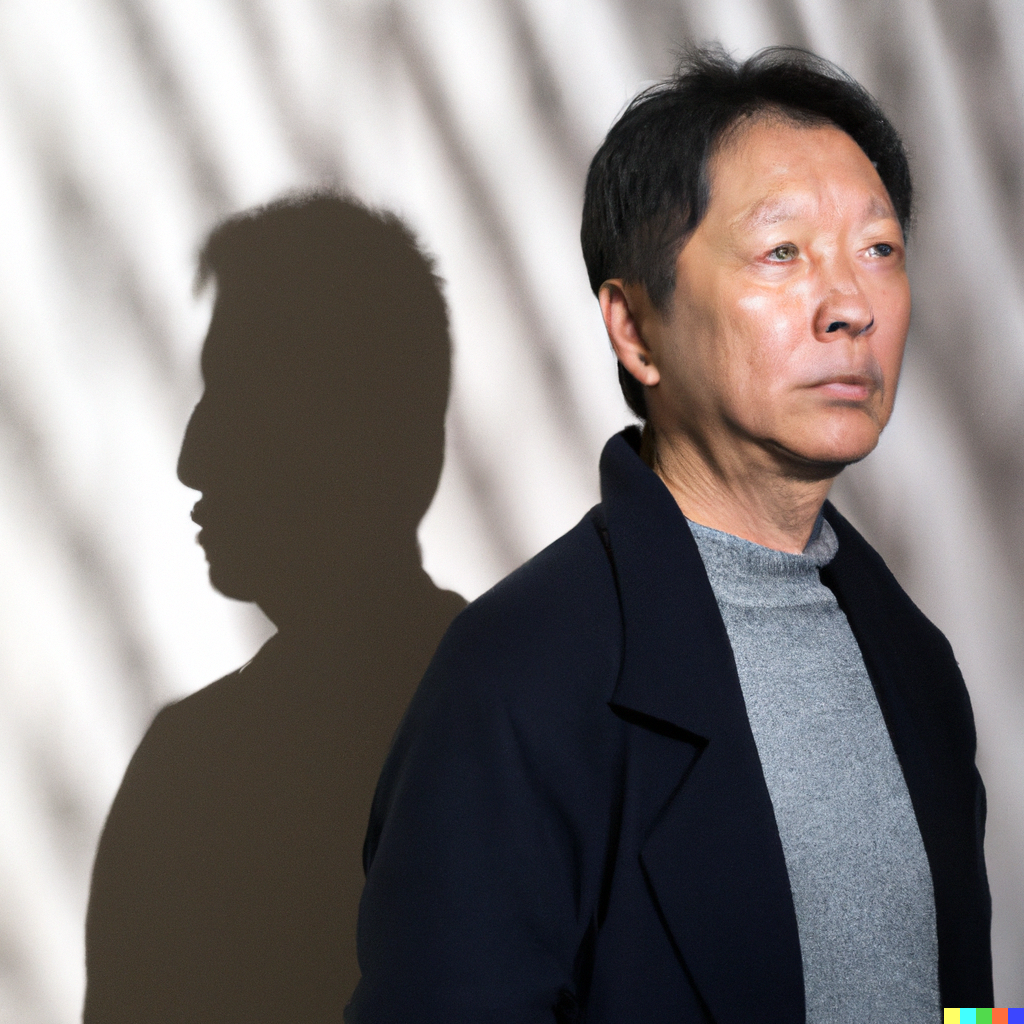
重盛律師的父親是個法官,他對重盛說,會殺人的人和不會殺人的人之間,有一條巨大的鴻溝,會殺人的人從出生就會殺人。重盛回說,這一番言論還真是傲慢。父親繼續說,認為人會輕易改變,才是真的傲慢呢。
重盛曾說,辯護是不需要理解的,但重盛並未真的就此放棄理解,只是那句不需要理解,反倒像是重盛為了理解他人的困難而做出的辯護詞。正是因為不能理解,所以需要辯護。
當重盛去北海道找了三隅的女兒,想要試著理解三隅內在那不可理解的事物,三隅的內在像是被點燃了,空空如也的器皿內像是有東西炸開來似的
三: 我也有些回憶是不想想起的,請迴避一下。
助: 不過我認為,人有必要誠實面對自己的行為。
三: 面對? 有嗎? 沒有吧,人就是要視而不見,不然不能好好活下去呢。
重: 無論如何,請不要用這種態度面對審判,陪審團。
三: 我知道的啊。
三: 這世上有些人就是不該被生出來。
助: 但是殺了他也不能解決問題啊。
三: 你們不是就是這樣做嗎。
助: 你錯了,這世上沒有不該被生下來的人。
重: 我個人不認同。生命的出生終始與個人意志無關。不能選擇自己的出生,有時甚至死得不明不白。
他的證詞在偵訊時反覆不定。他本身沒有怨念或仇恨,其實真是奇怪呢,像是空空如也的器皿。空空如也的原因,不知道是甚麼,是真相擺不下呢,或是同時像是個已經死去的自我詮釋呢
三隅總是很有禮貌的,問好,天氣,雖像是順應了社會有禮貌的要求,但在每一個監獄會面時,卻都像是不恰當地,突兀地,荒謬。(我做到了有禮貌的要求了吧) 正如他像個容器一般的行動,這誇張地顯示了順應要求的荒謬與無奈。
看到這邊,突然想起了法國文學家卡謬的異鄉人
1937年卡繆在筆記本上寫下最初的構想:「一個曾追求過著正常人生(婚姻、生活狀態,等等)的男人,突然發現,之於人生,他一直是個異鄉人。」
卡繆在薛西佛斯的神話這本書中說過類似的話: 「荒謬誕生於人類的呼喊與無法理解的世界的沈默,兩者之間的相遇。」或者這樣說:荒謬是「渴望的精神與令其失望的世界之間的離異。」”
荒謬的英文absurd,字源是拉丁文的absurdus,意為音樂上的「不合調」,在存在主義中用來形容生命無意義、矛盾的、失序的狀態。我想這牽涉到,人要如何理解自己與世界的關係。
關於人是如何發展自己與世界之間的關係,若從威尼克特的話來講起當然可能有很多不同的起點,而我想用溫尼克特在1945年的原初情感發展primitive emotional development中說: 人如何領會分析師及其工作,其實與他個人的狀態、病理很有關係。不同類的人對分析師及分析工作有不同的幻想。...正在尋求幫助他原始的、前憂鬱客體關係方面的人,需要他的分析師能夠看到分析師對他無可取代的、同等的愛與恨。
換言之,需要有人看到了自己的發展狀態,並且將這情感發展還給對方,否則無法進行下去。
在荒謬的感受之中,莫梭殺了一個阿拉伯人。行刑之前,莫梭對自己的內在世界做了整理,關於黎明的感受與自己的上訴。他聽著自己的心,最後對自己說,最通情達理的作法,是不要勉強自己。
異鄉人的最後一段文字中描繪,就在臨刑的前夜,他覺醒了:「面對著充滿信息和星斗的夜」,他「第一次向這個世界的動人的冷漠敞開了心扉」。他居然感到他「過去曾經是幸福的」,「現在仍然是幸福的」。他似乎還嫌人們驚訝得不夠,接著又說:「為了使我感到不那麼孤獨,我還希望處決我的那一天有很多人來觀看,希望他們對我報以仇恨的喊叫聲。」
對這一段,我的解讀,像是在說,對於世界與自己之間的荒謬,在此時,莫梭展現出一種情感的發展,而讓對自己與世界的大門得以敞開,或許是荒謬還是冷漠或是仇恨,但此刻感覺的自我情感,可以成為一種調和不和諧的過渡地帶。可以傾聽不協調音,而不去強求於威尼克特說的假我的順應性的成就。
或許作為這部電影中的異鄉人,三隅不得不詮釋自己是不應該,或無法出生的,這樣的出聲,來作為對自己命運的出聲,作為一種對命運的掌控與回擊,抗議。畢竟,我還是能夠對自己的人生做出最後的詮釋。這種詮釋或許是傲慢了。但在運命的全能感之下,傲慢一點,或許已是最卑微的願望。
生而為人的悲哀? 我一直是在世間流浪,空空如也,吃下世間擺放在我眼前的事物,世間告訴我的,就成為我。真相是甚麼呢? 放棄自我與成為自我,這理由是甚麼呢? 是甚麼生活方式,才能承擔住那生而為人的悲哀,或是哀傷。哀傷的感覺是還有一個主體能夠感覺受傷的感受,悲哀的感覺卻是只好空空如也的感受。
(待續)